从业十年的路口,我踩了脚刹车,停下了脚步,想好好琢磨琢磨往后的日子。
忽然一天想起了那些年并肩敲过代码、一起吐槽过老板、在会议室里为方案争得面红耳赤的人 —— 现在他们过得怎么样?未来又会往哪里走?
于是索性列了张清单,带着一肚子的好奇和几句没说够的再见,再次与他们相约。
S 公司 – 跨境打单和仓储管理
S 公司是做跨境物流和仓储这块的,在我待过的创业公司里,算是最有 “意思” 的一家。老板远在美国,隔着时差遥控国内团队,总爱带着我们琢磨国内外大厂的门道,大伙儿常常开着线上会议讨论业务走向,公司管理等各种话题,那种畅所欲言的氛围真的很不错。
公司爱尝试既是优点,也是缺点。大家认可的事,推进起来如顺水行舟;可遇上绩效强制分布、995 这类招人抵触的事,就像逆水行船般艰难。我正是在 995 试点的时候走的。哪成想,我的离开竟像块投入湖面的石子,漾开的涟漪意外换来了同事们的安宁。我走后没多久,995 就取消了,一切回归如常。
这次回访的第一站便是 S 公司。这几年他们虽也经历了一些风浪,裁了些人,但推门进去,熟悉的面孔依然不少。围坐餐桌闲聊时才知,他们如今的状态,活脱脱是程序员们口中的 “神仙日子”:从不加班,遇着大雨大雪就居家办公,每年还有额外的特殊事假,就连五险一金都按实发工资缴足(PS: 长沙很多公司是按最低标准缴)。
可安稳日子里也藏着隐忧。他们坦言,这般舒坦的环境,就像温吞的泉水,待久了怕再也适应不了外面的湍急。工作内容安逸得像在舒适圈里原地打转,技术上吃着老本,未来总像蒙着层薄雾,看不清方向。眼下最大的心愿,就是这样的安稳能久些,再久些,最好能陪自己走到退休。

H公司 – 医疗
H 公司做医疗领域,刚入职时真是人才济济,一派欣欣向荣,活像春日里的花园。没成想第二年就急转直下,管理上开始 “整活”,各种谣言像藤蔓似的在公司里蔓延,到处都飘着负面情绪的氛围。这是我头一回亲历公司从盛到衰的过程。
我当时是空降的前端技术 Leader,为了摸清团队、调动气氛,着实下了番功夫。好在团队里大多都是职场新人,甚至还有刚毕业过来的应届生,管理起来倒也顺畅,大伙儿配合得很。不管是代码走查、技术分享,还是团建活动,都热热闹闹的,没有老油条敷衍了事。
可惜好景不长,公司走下坡路后,团队打散重组,绩效方案朝令夕改,还搞强制分布,末尾的要扣工资。大伙儿的工作体验像坐了滑梯,一落千丈。谣言又四起,说高层要裁掉长沙团队,把业务挪去广州。我实在受不了这乱糟糟的状态,便离开了。
这次见的老同事里,有人早已跳槽。他们资历尚浅,还能耗得起,如今的状态倒不错:工作里有东西学就踏实干,有空了就捣鼓些小项目 —— 技术人嘛,本就该带着股子折腾劲儿。还有人未雨绸缪,试着接接私活、搞搞副业,为将来多铺几条路。生活上,有的刚步入婚姻,有的还在为爱奔波,各有各的节奏。
也有同事依然在 H 公司。比起年轻人,留下来的多是“上了些岁数”的,跟我同龄甚至年长,拖家带口,肩上扛着房贷车贷,像被绳子拴住的船,不敢轻易远航。公司的问题他们看得明明白白,也试着努过力,可到头来总像石沉大海,没了下文。究竟是公司制度的桎梏,还是行业本身的迷障?想来真是让人费解。
还一位 HR 朋友,我们在 S 公司认识,后来她来到 H 公司,把我也拉过来了。如今她另谋高就,做到中层,管理着十来号人。我们在她公司楼下,点了杯饮料,边喝边聊:聊工作,聊育儿,聊生活,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,我还打趣道:“摸鱼这么久没问题吗?”她笑答:“在这里打拼了几年,也算是有功劳簿,工作时间和内容可以稍稍自由些。可心里总像揣着块石头,说不出的别扭,像被什么东西拴着似的。”。
“可不是嘛,” 我接话,”打工的,哪怕做到高管,怕也逃不过这种感觉 —— 毕竟不是自己的船。话说,要是真不上班了,打算干啥?”
“可能去老公老家,用自家的门面开一家店。做做咖啡,卖卖甜品之类的。”她眼里闪着光,描摹着想象中的店面。我乐了:“是不是互联网人想开的店都逃不过咖啡、甜品?我之前也想过,哈哈哈,大概久经劳累后都偏爱那份精致闲逸吧。”
A公司 – 互联网安全
这是我在长沙的第一份工作。那会儿日子过得像杯温茶,不烫不凉 —— 需求来得不紧不慢,三年里几乎没加过班,闲得发慌时还得自己找活干。我差不多每年都要重写部分代码,试试新技术、新框架,团队也乐意给我折腾的空间,挺好。干了三年后离开,无非是为了薪资,或是想在技术上再往前蹦一步 —— 公司年年涨薪,但比起跳槽的涨幅,终究差了截。
这次拜访的同学,不仅跟我在 A 公司是同事,后来在 H 公司也共事过,只是在不同的部门。如今他从 Web 前端转行到游戏开发,按他的话说:“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,倒也新鲜。能从零开始琢磨新东西,挺好。” 这倒真符合他的性子。
我一直觉得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,爱阅读,爱琢磨,常有奇思妙想。比如他之前跟我分享过”一天只做一件事“的体验:看一天的电影,或是在海边发一天呆。听着就觉得妙。
当我问到未来的打算,他说得很坦诚:”走一步看一步,未来的事情说不准的“。语气里没有迷茫,反倒有种 “任凭风浪起,稳坐钓鱼台” 的笃定。
P公司 – 网站开发
2014 年刚毕业时,我在广州叩响了职场的第一扇门。那时的想法单纯得像张白纸:能挣够房租养活自己,能在代码里多攒点本事就好 —— 毕竟刚毕业,资历和能力都是短板。
说是公司,其实藏在小区的普通套房里。这是个三人小作坊,没有写字楼的玻璃幕墙,却有家常菜的烟火气。大家都带着股子随和劲儿,愿意蹲在同一个工位前聊技术,偶尔还会围在厨房炖锅汤、炒个菜。这里没有签不完的流程单,没有层层审批的 OA 系统,简单得像段无冗余的代码,高效又自在。虽是单休,但节奏松快,每天总能匀出一两个小时啃技术文档,像给亟待生长的树苗悄悄浇水。
在这儿待了一年,我最终还是回了长沙。和家人算过一笔账:在广州扎根买房,像要徒手搬开压在头顶的巨石,不如趁早回故乡土壤里扎根。
M 是当时的合伙人之一,比我大 10 岁,比我高半个头。虽说是老板,却半点没有架子,反倒像个爱唠嗑的邻家大哥。2015 年我离职后,我们像断了线的风筝,几乎没了联系。直到七年后的 2022 年,我在 H 医疗公司陷在焦灼里,像困在循环语句里找不到出口,忽然想回广州看看 —— 想去职业开始的地方,找找最初的平静,试着联系 M 时,他没半分迟疑就应了:”来呗,正好聊聊。”
那次见面,我请他吃了顿简单的便饭,他拉我去他开的店里喝招牌牛油果汁。那股子醇厚的香味,至今像存在味觉的缓存里,一想起就格外清晰。我们聊 P 公司的后续,聊他开的店 —— 要晒果汁,聊我这些年的辗转,话头像拧开的水龙头,自然得仿佛中间那七年只是按下了暂停键。
就在前不久的 7 月底,他带着家人来长沙度周末,我们又见了面。一起逛艺术馆看光影流动,钻进巷尾的苍蝇馆子嚼地道湘菜。他说这几年生意像走在颠簸的路上,身边朋友也常叹经济下行的压力,但话锋一转,眼里又亮起来:”刚瞅着个新地方,打算再开家分店。” 我告诉他,自己停了下来 —— 工作十年,想歇口气换种活法。原是他陪家人度假的行程,结果我俩在艺术馆的长椅上,从午后聊到日头西斜,像当年在小套房里讨论业务那样停不下来。
这种久别重逢却毫无隔阂的感觉,像把蒙尘的旧钥匙,轻轻一拧就打开了记忆的门。周日傍晚送他们一家上地铁时,我们笑着约好:”下次再聚”。

结尾
以上就是这次探访老同事的零星记录。我待过的每家公司,几乎都有几位处得投缘的同事。在我看来,工作要占去人生大半时光,工作体验重要,并肩作战的人更重要 —— 毕竟面对同事的时间,往往比家人还多。若能从冰冷的 “同事”,处成共事的伙伴、生活的朋友,那便是职场里的幸事了。
一圈聊下来,心里更亮堂了:
人生从无标准答案,各有各的路,各有各的精彩,自己走出来的路,就是对人生最好的回答。
所以往后,我会更多的向内探索,问问自己:想成为什么人?想成就什么样的事?想过怎样的一生。
目前,我的自由职业先从自媒体起步:公众号写写文章,把过往的经历和思考摊开来讲;B站做做视频,分享我模拟赛车的比赛经历。能不能挣钱?不好说,但我知道,这两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有价值的,有意义的,而且是打心底里喜欢的 —— 做起来没什么心里负担,抬手就能开始。
做自媒体像是种下一了颗无名的种子,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长大,开什么花,结什么果。我能做的,就是带着欢喜和期盼,小心护着它长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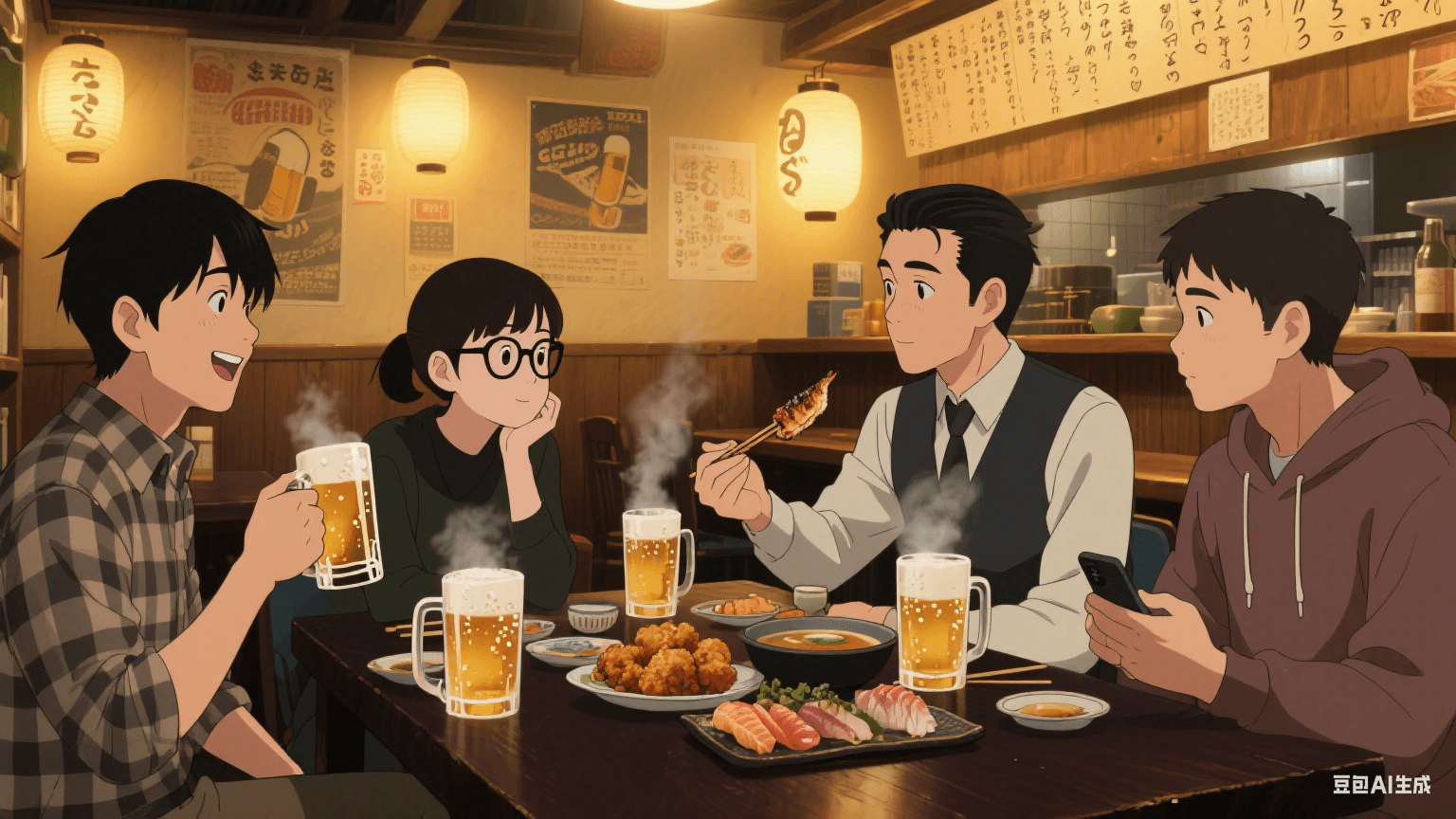
发表回复